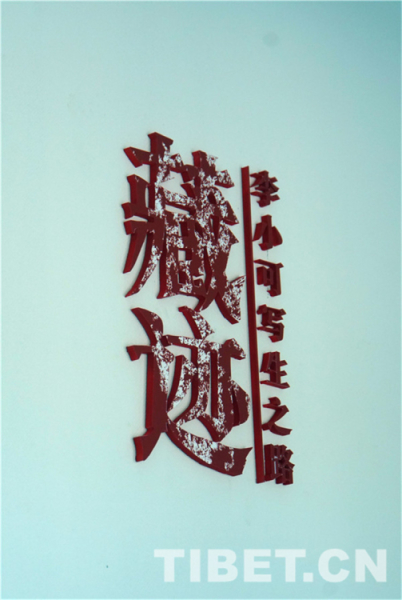
圖為“藏跡——李小可寫生之路”展入口 攝影:王茜
中國西藏網訊 作家馬麗華曾在《經由小可的眼睛》一文里寫道:“只是在凡器世間他(李小可)比家父多走出了一步,自從他發現了西藏這個地方,藝術和西藏就成了唯二的話題。一旦開了頭就像摁下了語音鍵一發而不可收,平素的抽象也頓時生動起來,六神歸位,情有所依,心中涌動熱情,眼里充滿光彩,智商和情商得以充分展現。”她感嘆“這是小可的西藏,或說是非同小可的西藏。”
在畫家李小可眼中,“藏地大自然的純凈博大,蒼茫;藏族人的真切摯熱,剛悍和淳樸,給我以震撼。在當今繽紛物化的時代里,藏地藏族人那種本源狀態給人帶來了生命的感悟和靈魂的洗刷。”日前,“藏跡——李小可寫生之路”展在北京李可染藝術基金會美術館開展,透過三十年來三十四次入藏經歷的一張張作品,經由李小可的眼睛發現非同小可的藏地印記。而對于李可染藝術基金會秘書長、李小可夫人劉瑩來說,這三十年的結緣,帶給她的卻是非同小可的愛恨交織。

圖為李小可夫人劉瑩導覽李小可畫作 攝影:王茜
劉瑩為記者分享了李小可跟西藏結緣的故事。“1988年,攝影家鄭云峰要赴黃河源采風,詢問李小可去不去,家里人都沒有同意,他還是偷偷去了,一去就是45天,還在那里矗立由父親李可染題字的‘黃河之水天上來,奔流到海不復還’的石碑。從此,赴藏之行開啟,一發不可收拾。”劉瑩語氣頗為無奈,“他去西藏幾十次,對于我來說真是折磨。”

圖為參觀者觀賞李小可畫作 攝影:王茜
“幾十年以來,除了幫助父親做事,李小可一有時間就一定要去西藏。當時去西藏是坐飛機到拉薩,然后坐汽車去目的地。開始都租不起車,基本一路走一路搭車,后面經濟條件稍好后可以租車,但這租車的費用非常高,還是不夠。有時20天都不聯系,突然打電話來說馬上給他匯一點錢,我基本上手上有多少就給他匯多少,但是匯款畢竟不如現在方便,不能及時到款,他又非常著急去某個地方,只能先欠人家的錢,三千五千的車費在當年就是天大的數字,考慮半天,他將帶的三個照相機賣掉一個。后來,賣相機換車費的事情年年都有,一年里畫畫稿費全都用在這上面,我在家除了日常花銷,剩下所有錢都給他,但這些不算折磨。真正折磨我的是他一走三五十天沒有消息。”劉瑩語氣微微哽咽,這樣的回憶想起來還是揪心和后怕,“這個太折磨了。我最難受的就是1990年他去長江源頭地區采風,說好不去的,而且他父親也不愿意讓他去。我是工作時突然收到電報:‘很想念你,我現在向格拉丹東方向前進’。這才知道他們又偷偷去了。因為我以前在中央社科院院刊上了解過,長江源北麓到格拉丹東是多么艱險,可以稱得上生死旅程。我當時心里咯噔一下,心想完了。”

圖為劉瑩介紹李小可三十載入藏的傳奇經歷 攝影:王茜
接下來杳無音訊的45天里,劉瑩一下掉了八九斤體重,李小可的母親也曾想通過軍區搜尋他們的蹤跡。幸運的是,李小可平安歸來了。再回想當時徒步在格拉丹東的11天,踩在牛踏上去就陷到腿肚子的松軟凍土里的危險,三張普通棉布白床單搭建的帳篷,看著迎面走來都黑瘦得認不出來的李小可,劉瑩既心疼又后怕。如此艱難危險的環境,偏偏遇到摯愛高原火熱的一顆心,作為家屬,也不得不欽佩李小可的藝術情操,也為他筆下的西藏感嘆、震撼。

圖為李小可作品展現場 攝影:王茜
李小可為了尋找新的繪畫語言和感受,曾多次到藏區,歷經青海的黃河源頭、長江源頭、柴達木、西藏的阿里、珠峰、那曲、甘南的瑪曲、碌曲、夏河……三十載的堅持,多少吃苦多少堅韌成就了現在的他。可是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卻總謙遜地說“我企圖走得更近,可它永遠在遠方”。“從黑頭發的帥小伙一直到白發蒼蒼的老頭兒,李小可無論成就多么高,卻不高調,一直保持謹慎、謙和。我總說他趴在地上都覺得自己高,要挖一個坑進去才行。”劉瑩略帶調侃地說,“所以李小可曾經七次入藏到珠峰都成功地見到了珠峰,最長也就等過幾十分鐘,每次都創作了非常好的作品,跟西藏的緣分就像幾輩子修來的。”(中國西藏網 記者/王茜)

圖為參觀群眾觀賞李小可作品 攝影:王茜
版權聲明:凡注明“來源:中國西藏網”或“中國西藏網文”的所有作品,版權歸高原(北京)文化傳播有限公司。任何媒體轉載、摘編、引用,須注明來源中國西藏網和署著作者名,否則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。